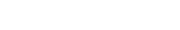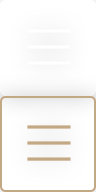余姚建造余上慈闸始末
余良奎口述 丁唯真整理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那会儿我在余姚县从事水利工作。当时,宁波、绍兴行政上还没有分开,新昌、嵊州、诸暨都属于咱们宁波的地界。那时,新中国成立不久,水利事业刚刚起步,很多思想观念仍旧停留在农耕社会的经验积累上。就拿“蓄水”来说,传统上对梯田以“水娘田”(在梯田中选择一块田,不种水稻专蓄水以灌溉周围水田)方法解决;对沿海塘田,以稻田深蓄水解决;对平原地区,深挖水塘,靠降雨蓄水,名为“平原水库”;或沿丘陵,筑低堤以蓄水等等。
宁波虽然是靠海,但地处(上)虞余(姚)平原的余姚却不得不从曹娥江引水使用。当时,引水的主要渠道就是曹娥江的右岸的“引曹济姚”工程之一的广济涵洞。历史上每逢大旱,余姚的农民就背锄带铲,开启曹娥江塘下的广济涵洞,引江水入河,再涌至上虞与余姚交界的河清堰,扒堰放水以救枯苗。不过,广济涵洞最大引水量仅12立方米/秒,灌溉上虞农田都已勉强,若余姚再去引水,就属于抢水的性质,所以说这一带就发生过械斗事件,水利纠纷更是层出不断。况且,广济涵洞先天不足—地势上,它是东高西低,余姚一侧进水水平线在余姚城区之上,这样引水过程中一不小心,整个余姚就可能被淹没。引水始终存在隐患。
记得1951年余姚又发生干旱,河水几乎干涸。经农民强烈要求,报宁波专员公署同意,派专人负责去上虞,协商开启河清堰放水一事。当时,就让我跟随余姚民政科同志去上虞办理这件事儿。好说歹说,上虞方终于同意,由上虞农民动手,把河清堰扒开个宽3米、深半米的口子,放水18小时后,再还土堵住。
“杯水难以解久渴”,问题只是临时性地解决。我们都意识到这绝非长久之计。为了能长远解决两县水利纠纷,有效灌溉农田,余姚水利局提出了兴建从曹娥江引水的进水闸的方案,经余姚县政府上报宁波专署。宁波专署领导非常支持,立即审批通过,还专门下发建闸通知,强调:一定要精心设计,一定要造得牢固,一定要在一冬春建成。并决定,由余姚县负责施工,建闸所需人工、材料、费用均由余姚县承担。就这样,建闸任务就落实到了余姚县水利局,我开始负责这项工程的建设。
当时,建闸的费用主要靠收缴过船费自筹,不够部分才由财经拨款解决。人工都是余姚当地的技工。建闸地,选在了处于半棉半稻区。当时余姚水源附近的地都用来种上了水稻,而紧挨着慈溪的所谓干旱区则用来种植棉花。
工程第一样,闸址旁的一座石灰窑首先要拆除。起初,我十分担心窑主不肯拆而影响工期。谁知,与他一谈,他竟是马上同意了,提出的赔偿要求也合情合理,心里着实感动。后来,我侧面了解到:原来解放前,他运石灰到余姚去卖,船过堰坝时,经常被堰坝头敲诈;任凭他苦苦哀求,也无济于事。要知道,生石灰遇水就报废了,这一船真是血本无归呀,害得他几乎破产。解放后,实现公有制了,再过坝,收费公道,通行便利。记得有一次,他又遇雨,堰上的工人马上找来竹簟,帮他遮盖那些生石灰,所以,他对人民政府心存感激啊。现在,政府要造闸拆窑,他大大拥护还来不及呢。在接下来建闸过程中,他还主动做村民们思想工作,使我们的工作顺利不少。
有了群众的支持,我们的干劲更足了。大家动脑筋,开思路,想出不少好点子来。比方说就地取材方面,有些同志就提出就近拆除临山卫的城墙,拿现成的条石作为闸身用料,走水路,用船装运到百官工地。这样既快又牢又省钱,工期也大大缩短,上级部门也同意了。要知道,当地的余姚石匠技术高超,现成的条石稍加处理,就能够建成牢固的闸身了。而对于地势上先天不足,无法实现直引的状况,我们提出了“四个阶梯构想”,即在上虞——驿亭——余姚——慈城——宁波分层建设引水渠,一阶一阶引水到宁波,最后排入甬江。
利民工程,一呼百应,咱们施工队就有近200人,都是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。上级领导也很重视,经常下来检查工期进展。施工中,我们一有问题提出来,县长、区长马上来现场办公。就这样,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,1954年5月,一座三孔的进水闸终于落成了,它被定名为余上慈闸,它的闸孔总宽6.6米,足足比广济涵洞大了三倍。余上慈闸建成后,灌溉区域遍及上虞、余姚、慈溪的百官、崧厦、小越、马渚、临山、低塘、四门,周巷、长河9个区的44万亩农田。后来为提高引水能力,我们又组织三县农民,全面疏浚河道,拓宽阻水桥梁,整修边界涵闸。疏浚后,每年伏季7-9月,引水量大时可以达到5000万立方米。为了测试引水的最远距离,1964年冬,我们还专门开进水闸,引水测试。结果发现,在久晴无雨的情况下,宁波的姚江大闸水位的确有所上升。这以后,民间便有了“曹娥江水曾到过宁波”的说法。
但是,引水也引发了河道淤积的问题。由于进水闸口在曹娥江的中下游的咸潮河段,引水中悬移质含量高,入内河后,就沉淀在进口段的上虞县,虽然组织过几次挖掘,仍不能治根;而且挖土堆土,损占农田,引起当地农民的反对。1982年,余上慈闸身底板开裂,为确保安全,临时封闭。那时,在进水闸口上游的上浦,已拦江建了上浦引水闸,实现向曹娥江引水。这样,我们决定永久封闭余上慈闸。曾引水泽被44万亩农田的余上慈闸,历经30年,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如今我已近90岁了,回顾这段经历,我最深的感受是:治水固然要依靠积累的实践经验,也要结合实际水况,摸准水的规律,科学治理。